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
回顾即将结束的这一年的读书生活,仍不得不让人感叹“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不仅自己购买的许多书至今都还没有读,许多师友寄赠的大著、新刊同样未能悉数拜读完毕,要写的文章、要修订的几部书稿也都没有完成,只能留待以后。因此,以下的片言只语,虽立足于厕身的中国文学专业,不敢“跑野马”,但也只是一些个人初步的、粗浅的、对本年新出部分研究著作的阅读感受,疏漏、悖谬、孟浪之处均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匡我不逮。

首先也许应该谈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黄修己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全书五大册、一百多万字,从五四新文学初创期一直写到新世纪的研究进展,作者姚玳枚、陈希、吴敏、刘卫国,均为师从黄修己先生、学有所专的中青年学者。其实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及其修订本,到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再到五卷本的《通史》,黄先生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高度也正由此得以不断确立。这套书问世后,我和中山大学的师友联合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在线对谈会”,进一步较深入地讨论了其学术贡献及有待发挥的地方,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和会后同仁们的申论,即将或已经在不同刊物发表,此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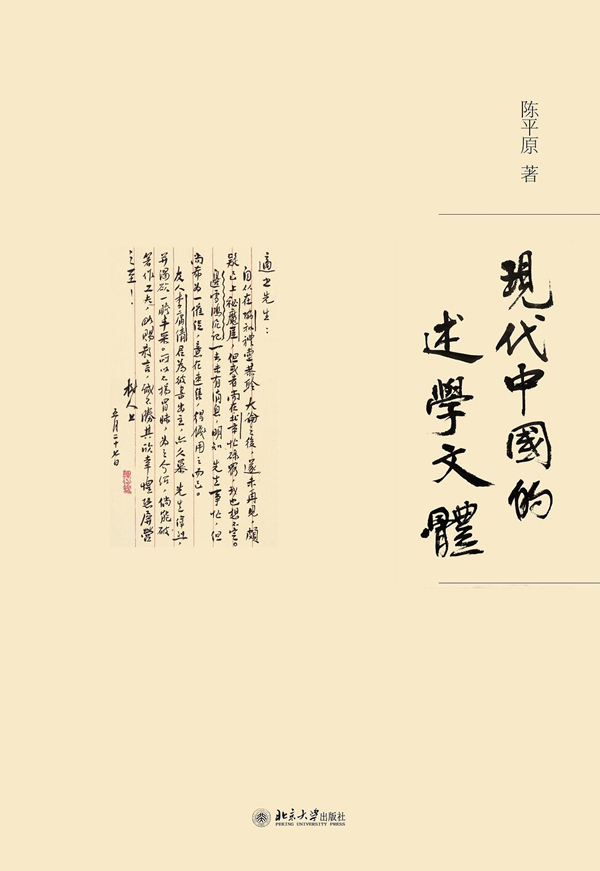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也是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部书。该书各章此前多已在学术刊物发表,早已拜读过,但都为一编且改为专书体例之后,仍可见出作者对此问题思考的系统性、广度和深度。事实上,从晚清至今,中国人文学者的著述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变化、转型尚未完成,今天我们仍能时常听到诸如关于“西式论文”“西式规范”等是否适合中国人文学术的讨论,就此而言,无论是蔡元培、章太炎的文体意识,还是梁启超、鲁迅、胡适的学术文,这些现代学术先驱的思想遗产,对于今人如何确立言说的立场、方式与边界,或都有一探再探的价值。此外,作者今年还出版了《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年3月版),内收其论文、著作、随笔、书信等手稿多篇。当代学人出版手稿者,坊间尚不多见,此书不仅印制精良,所选篇什也多能代表一代人的学术旨趣、精神气质和立场追求,当然也有压在纸背的“人间情怀”。尤其从家书这一较具私人性的手稿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治学、治生的不易,和面对不甚安定的外部环境时仍能葆持的一种乐观、自信、深耕学术的心态。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其先后贡献出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等多种重要著述。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愈益自觉,逐渐有分裂成为一专门学问领域的趋势。《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陈子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的出版,为此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治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年,著述等身,是次应复旦大学出版社“名家专题精讲”丛书邀请,将历年所作重要文章,按作品版本研究、集外文和辑佚、手稿、笔名考定、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史实探究、作家文学活动考略、现代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十个方面,加以遴选,试以不同例证、不同个案的研究揭示此一领域研究的堂奥,凸显“实践性”优先于理论生产的重要,足称金针度人。在其近两年出版的《说郁达夫》《说徐志摩》《梅川序跋》等书中,作者也相继提出了发展“徐志摩文献学”“张爱玲文献学”等现代文学文献学分支之分支的设想,可见其对文献研究体系、理论方法的思考虽未结撰成专论发表,但仍在持续进行之中,且有相当激进的一面,不可不察。另外,今年秋天我也编辑了一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教授荣休纪念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20年9月版),对这方面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可一并参考。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重溯新文学精神之源: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晚清思想学术因素》(李振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该书采用“内烁型”的研究思路,细细爬梳新文学传统与晚清学术思想史的关系,所见极为深刻。其中更不乏研究者强烈的主体性和当代意识,是一种有抱负、有情怀、有现实针对性的学术。当然,藉此我们也许还可以讨论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思路、晚清的学术思想和晚清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新文学的独创性品格究竟为何、如何看待不同于危机时刻的学术想象的“纯学术”、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本书未征引相关著作的研究等一系列问题。此书出版后,友人金理教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我们的发言也将于近期集中公开发表。

本年除了上述这些资深学者仍在持续贡献新作,中青年学者的大著仍出不少,其中不少都是相熟的师友,多有驳诘往复,无须辞费。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康凌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不仅是从听觉文化的角度研究左翼文学、文化,而是研究左翼文学、文化,却没有被既有的左翼研究思路框住、拐跑,相反,扬榷而陈之,是从一种新的批判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1930年代左翼诗歌对音响形式的经营和其中内蕴着的感官动员技术。换句话说,作者研究左翼,但他的立场不是左翼的,他的思想预设、出发点和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并不是要重新回归左翼(当然也不是非此即彼,倒向新自由主义),更不是想要维护某种绝对主义的运思方式和自以为真理在握、在道德和审美立场上处于强势地位的论述策略,而是为了拓宽左翼文学的诠释空间。但站在充分的后设的立场上,如何看待朗诵诗等左翼文学的“文学性”(难道仅是一个特殊的认知装置?或流行的“文化政治”概念就可以取代、解释?),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特别是在教学、文化传习中,一首满坑满谷战斗口号的诗歌、一篇写生产队挖地开荒的报道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文系之外的读者所接受?又能够流传多久?何以证明其丰富的“生产性”不是一套特定的学术话语(意识形态)、惯习的自我建构和不断增殖的过程?这些问题似仍值得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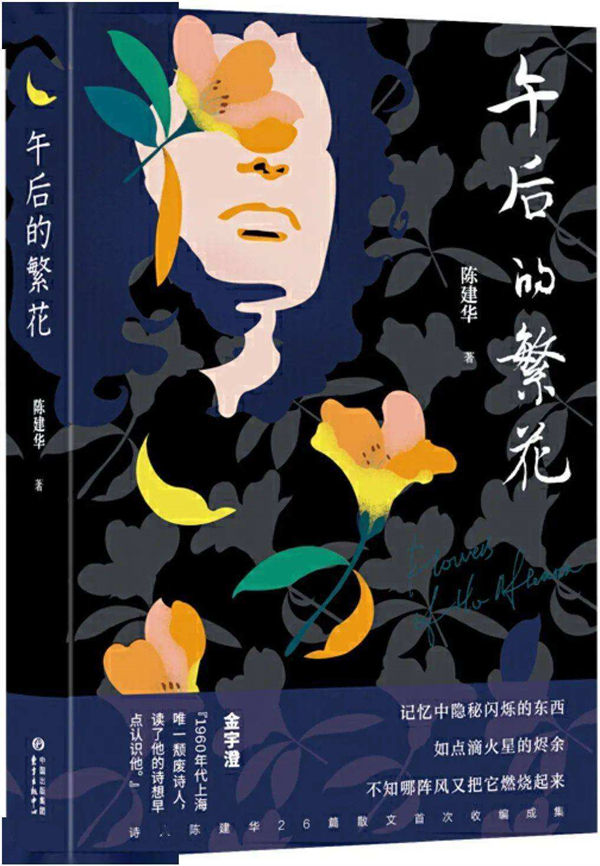
专书之外,几种新出的关于近现代文学、历史、电影、艺术的随笔集也很可一说。《午后的繁花》(陈建华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版)中,所收不仅有其近年新撰如《文以载车》《陆小曼·1927·上海》等佳作,也有首次结集出版的二十余篇散文和学术随笔。但无论是对民国电影史的重探,还是对清末民初文学与思想的重访、物质文化研究、视觉文化研究等,抑或是关于新世纪一度流行的“狼文化”的批判,乃至其追忆师从李欧梵先生及纽约读书经历等等,都带着“老克勒”不懈探寻“诗与真”的明显标记,这些“记忆中隐秘闪烁的东西/如点滴火星的烬余”,见证了学者之外作为诗人、作家的陈建华的另一面相。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读《陈建华诗选》及作者其余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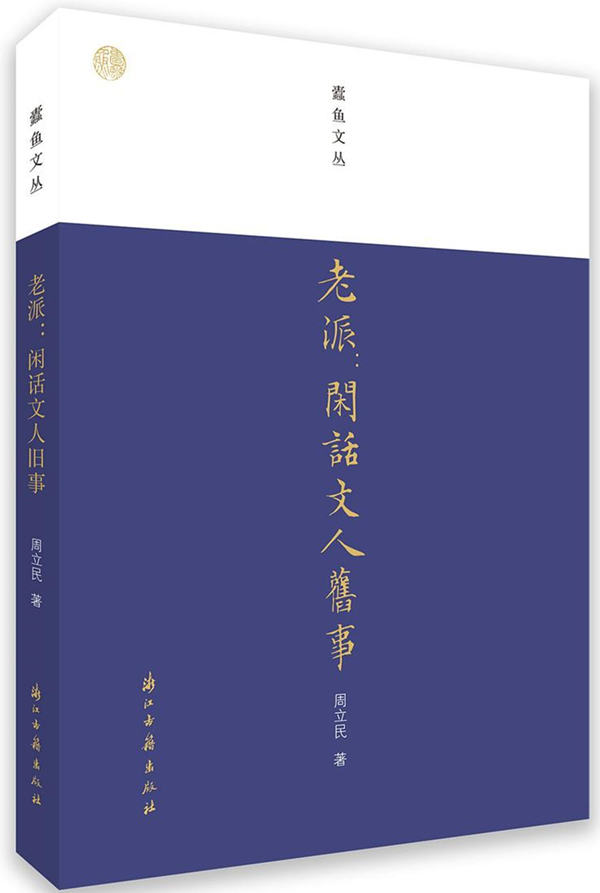
《老派:闲话文人旧事》(周立民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星水微茫驼铃远》(周立民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版)是作者在《传记文学》等处的专栏文章、随笔、读书笔记的集合。前者各篇篇幅较短,后者诸章论述更从容,但无一例外体现出作者因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兼以勤于读书、敏于思考,虽是论文述史却不偏执一端、笔端仍饱含感情等鲜明特点。在其附录的《从“不好看”说起——学术期刊与学术文体》一文中,作者透过对当前学术期刊论文尤其“学报体”的批判,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研究、写作信念,乃是企图恢复人文学术写作的多元性,试验其间存在的多种可能,于我心有戚戚,而这一点不仅对于某种程度上已经僵化了的当代学术文体的革新具有警示意义,也再一次在事实上回应了陈平原的相关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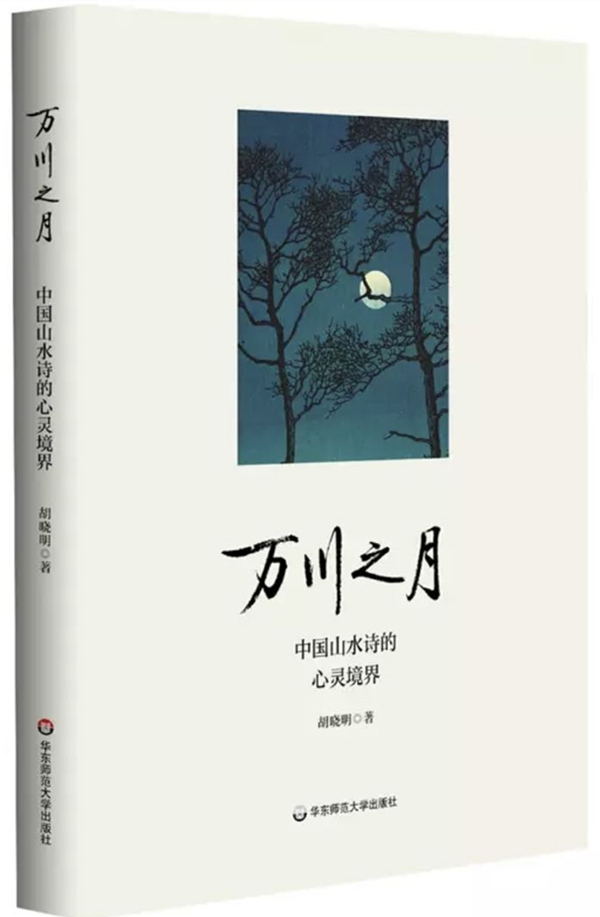
古典文学的书今年读得不多,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种。一种是《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胡晓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版)。这是作者的名著,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版,新世纪初期又出过一版,今年又出一新版。全书认为山水诗“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除了表达诗人的心境,更是表达着中国诗人代代相承的共通的心境,集体的意欲;这共通的心境与意欲,正映射着中国哲学的真正性灵”。因此,山水诗就不能仅仅被看作“精妙优美的语言文字或风景画”,还应探究其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心灵境界”,发现其中“隐藏在技法、家数、渊源、流派以及风格背后的共通的民族文化的诗心”。因此从雪夜人归、啼鸟处处、花泪蝶梦、荒天古木等十个方面,依次论述山水诗中映现出的生命的漂泊与安顿、悲哀与复苏、有我与无我、荒寒与幽寂等主题。但作者的论述并不是纯理论的空转,而是建立在对两百余首山水诗作的细致赏析与精妙解读之上,也很好地平衡了对诗歌文本的细部论述与对中国山水诗及其哲学、美学意涵的整体理解,从中不难见出作者重建后五四时代中国文论的努力。例如这样的一段论述——
“山水诗满足什么样的心理欲求呢?只要看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有那么多的宁静安谧的村庄、田园、古刹,只要再看看最早的山水诗,其实是对不自由人生的一种逃避,我们不妨认为山水诗是一个最大的补偿意象(compensatory image),尽管诗人们的真实命运中,充满了颠沛流离和不安焦虑的因素,他们对山水的崇尚心理,扎根于一种对更自由、更永恒、更真实的人生形式的持久的精神追求之中。宋人有两句诗:‘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其实,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处隔水相望的‘淡烟修竹寺’与‘疏雨落花村’。尽管山水诗语言、风格有各种变化,但其中所代表的那一份普遍的精神需求,却绝不会消失。”

另一种是《诗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孟留喜著,吴夏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这本书从表面上看,写法比较传统,自为袁枚得意女棣屈秉筠编纂年谱始,至订成袁枚所有女弟子年表结穴,依次讨论了屈秉筠的时代、家乡及家庭背景,社交网络,理论主张及两类代表性诗歌(家庭诗和关系诗)的创作特色等面向,有点不太像是一般我们想象的“海外汉学”,但在具体的论述、分析中,仍不乏洞见。如在分析其家庭背景时,提出了“家庭变成文学之网”这一重要观察,让我们想到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张氏三姐妹、林徽因和邵洵美的客厅、上海马斯南路曾朴的文艺沙龙、北京慈慧胡同朱光潜宅的读诗会……评析其理论主张时,则发现屈秉筠的家庭文学圈和包括袁枚女弟子在内的虞山圈的存在,已显示出一个因诗歌传播而缔结的“女性诗歌评论共同体”;由此体现出的所谓的“诗歌之力”或“女性诗歌之力”,从理论角度看,乃是女性生活、体验构成其艺术实践之动力,具体而言,正在于屈诗“使复杂的家庭关系简单化,使周边所有人和她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使其本人受到本地区内外的人的广泛的仰慕。”
尽管这一研究结论可能并不惊人,但对于我们如何研究一位不甚知名的作家的生平著述,这本书仍能予人很大启发,也再一次向我们给出了一个不同于何炳棣“做第一流学问”的思考方向:或许并无二三流的选题,只有二三流的研究。也正如在艺文创作中,“怎么写”远远比“写什么”要重要。
链接地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30277
